接下來,我們不妨分析一下此人的生活方式。首先,我們要從他的人生中找到一件和他當前態度有關的事,這件事得要從他最初的童年記憶中找。不過我們必須承認,童年記憶的價值很難確定。這個男人最初的童年記憶是這樣的:母親帶著他和弟弟到市場買菜,市場裡人多,摩肩接踵、嘈雜混亂。
母親把他抱了起來,結果不一會兒又把他放下,抱起了弟弟。原來母親一開始想要抱起來的就是弟弟,之前抱他是因為搞錯了。他當時只有四歲,被四周的大人擠得東倒西歪,非常害怕。在敘述這段記憶時,他帶著埋怨的神情和口吻,這表明他不確定母親愛不愛他,他嫉妒弟弟得到了母親的愛。
他當前的性格特點在這段童年記憶中已經有所體現,這進一步證實了前面的論述。我們解釋了他當前的狀況和童年記憶之間的連繫,他非常驚訝,並立即看清了兩者的關係。每個人都是在一個共同目標的指引下行動的。至於這個目標究竟是什麼,要看童年的生活環境給他留下了怎樣的影響和印象。
在成長的過程中,這些影響和印象會讓嬰兒迅速確立一個明確的人生態度和獨特的行為模式。每個人的理想狀態,即目標,可能是在他生命的最初幾個月形成的。因為人的部分直覺已經足以使稚嫩的嬰兒產生快樂或不快的情緒。
他們表達喜怒的方式或許極為原始,但心靈早就開始發揮作用了。總之,人早在嬰兒期,心靈就已經開始接受外界的影響,並作出反應。當時的目標將牢牢地在他心裡紮根,並不會隨著之後生活方式的巨大變化而輕易發生改變。
心靈的能力是為了適應社會
人每天都要遇到各種問題並加以解決,人心是衡量問題、選擇路徑的主導因素,所以人心絕不能,也不會是自由和盲目的。心靈只有參照了社會生活規律,才能判斷、解決問題。所以,社會生活對個人影響極大,個人卻很難影響社會生活,即使有所影響,範圍也很有限。
社會生活有兩個顯著特點:複雜性和多變性。當前的狀態永遠不會是它的最終狀態。因為每個人都必然要受到社會生活的影響,和社會生活產生複雜的連結,如此一來,人心也就複雜和隱密起來,沒人能真正看穿另一個人心底的秘密。
想要衝破人心難測這個困境,唯一的辦法就是把社會生活邏輯視為世界上一條終極的絕對真理,堅信只要逐步解決由社會生活—主要是個人能力和制度的侷限—所引發的各種問題,就能越來越靠近絕對真理。馬克思和恩格斯詳細闡述了社會物質層面的問題,我們需要仔細研究他們的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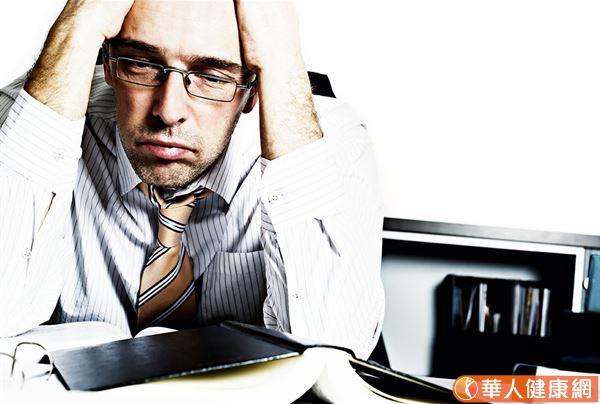
 拍打功打到瘀青、岀痧才有效?中醫師來解答,14類人不建議胡亂嘗試
拍打功打到瘀青、岀痧才有效?中醫師來解答,14類人不建議胡亂嘗試
 一覺醒來嘴歪眼斜,以為中風了…竟是顏面神經麻痺!中醫針灸穴位修復受損神經
一覺醒來嘴歪眼斜,以為中風了…竟是顏面神經麻痺!中醫針灸穴位修復受損神經
 核桃不只護心 還能從「腸」保健康!研究:吃核桃有助預防潰瘍性結腸炎發生
核桃不只護心 還能從「腸」保健康!研究:吃核桃有助預防潰瘍性結腸炎發生
 年後體重飆升是脂肪?還是水腫?醫揪3點原因,拆解「假性肥胖」真相
年後體重飆升是脂肪?還是水腫?醫揪3點原因,拆解「假性肥胖」真相
 孕期補鐵全攻略:血基質鐵吸收率佳,搭配葉酸提升黃金保護力
孕期補鐵全攻略:血基質鐵吸收率佳,搭配葉酸提升黃金保護力
 經期後容易缺鐵,補鐵做對了?營養師:聰明補充血基質鐵,恢復元氣好氣色
經期後容易缺鐵,補鐵做對了?營養師:聰明補充血基質鐵,恢復元氣好氣色








 闽公网安备 35020302001899号
闽公网安备 35020302001899号
